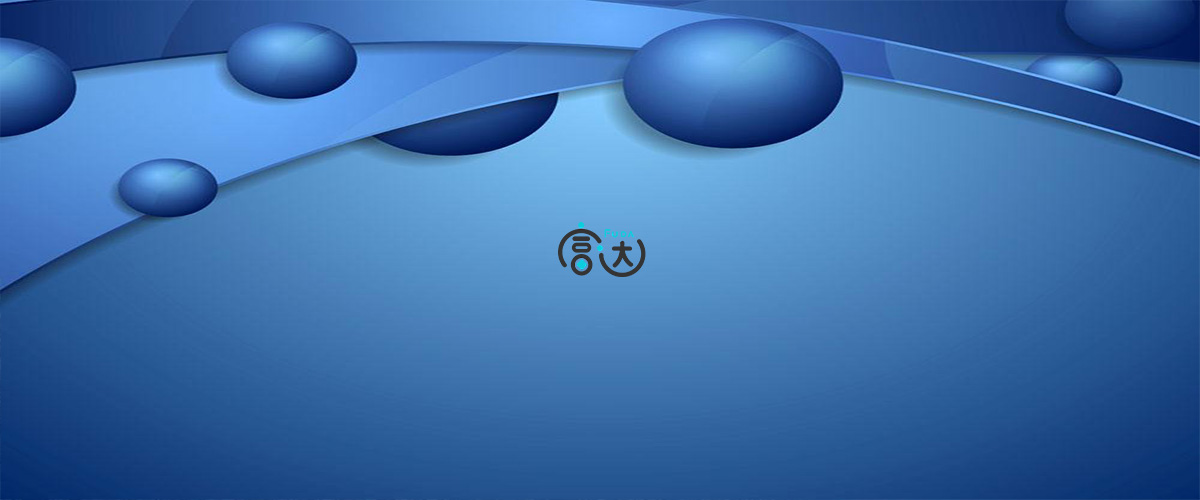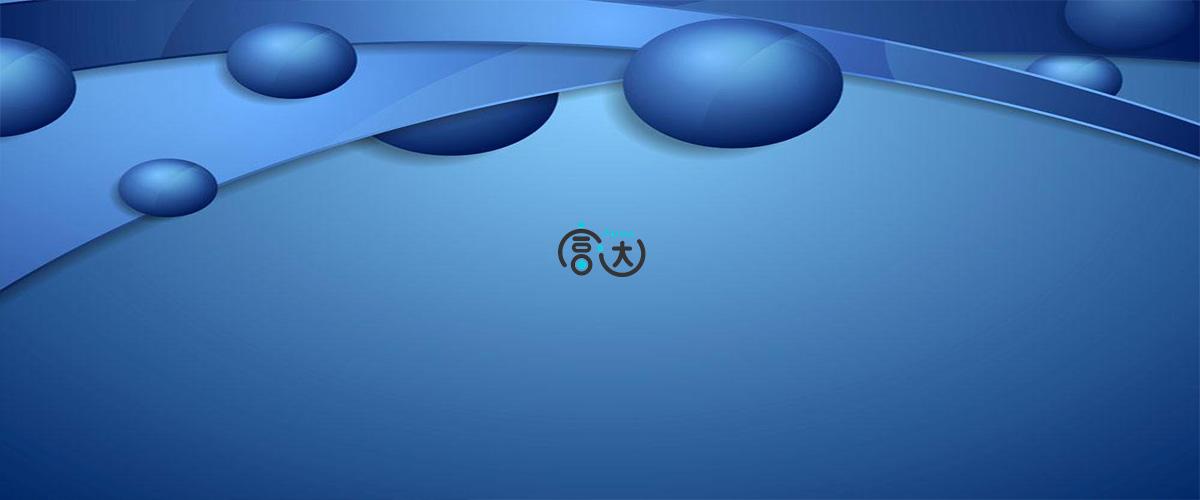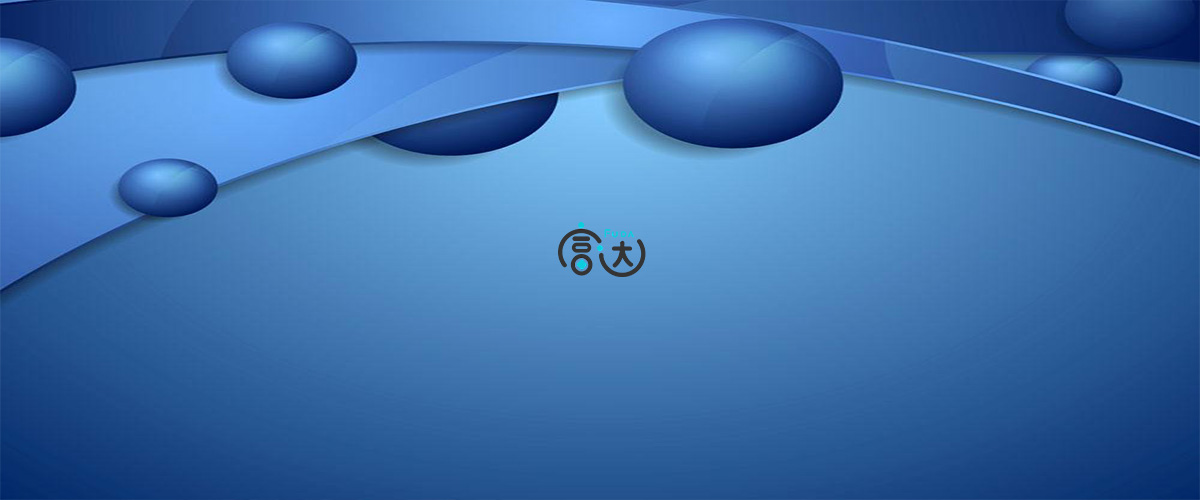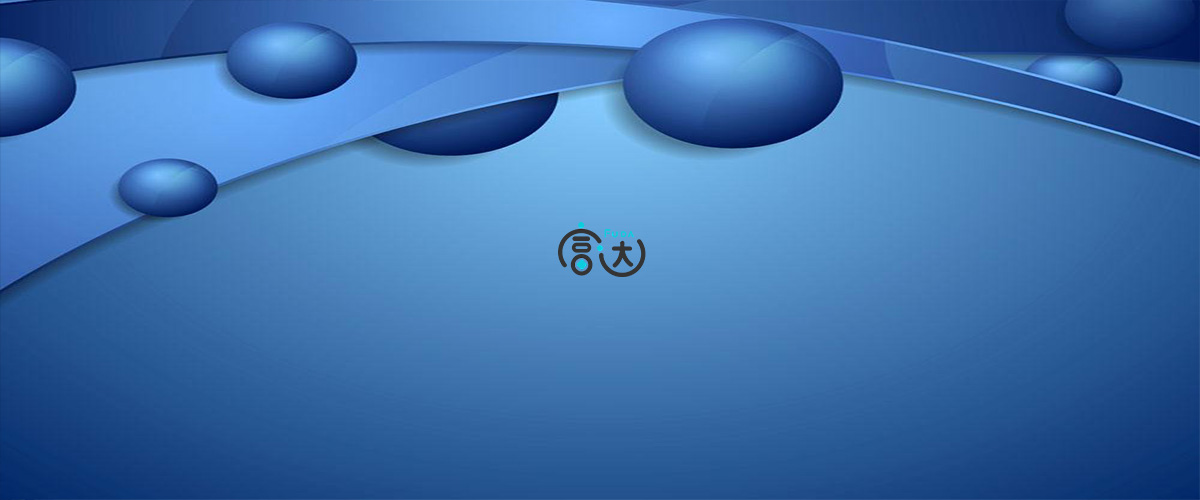富达|宋长征:2018,送别,兼与知交
富达注册报道:
天冷了,雀入大水为蛤。这是一个古典的意象,云雀在天空飞翔,蛤在泥涂孤单行走,谁能知道自己的明天呢,或者说即便当下又该如何把握?这是一个惯常的问法,答案千百万种:善于蛊惑者会说,努力吧,英雄的纳特耐尔一定会实现;现实者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梦想者从梦中醒来,那张可以套在脖子上的大饼子还没烙好——该怨谁呢?不是每个人的爹娘都是腰缠万贯的贵族二代。
姐夫走的那日,我始终不愿去医院,怕看见日光下的真实。一个勤劳的乡下汉子,用血用肉,用健康换取了少量积蓄,最终还是希望夭折在盛年。春天冬天运输鸡粪,常去的地方是梨花之乡砀山,鸡粪与梨花的浪漫和梨子的爽脆、清冽,就这样产生了关系,三姐也相随,至少劳累的时候可做替换;夏天开始,奔忙于建筑现场,为人间造房子——这样的工作不需要任何艺术细胞,也不需要秉承一颗济世之心,踏踏实实的砌砖、粉刷,能把房子不盖漏水就好,要不主家会在之后的几年中喊去返修。改装的五轮机动车,除了运输鸡粪之外,另兼买卖粮食,夏收秋收,会把麦子玉米倒腾到粮食点,以赚取可怜的差价。
这是竭尽所能的付出,为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而努力,当然是希望换取一个美好的明天。买东西时,我们可以说:我只割十块钱的肉或者我只买手中这些钱的。看病时姐夫也这么说:我只治疗十万块钱的。没有更好的建议,我们去不起北京上海美国澳大利亚,只能从县城转向省立医院……白费心机,四个字里包含着太多不忍与无奈,谁愿意看见亲人眼睁睁在盛年消失?
吃人的木头和机器。曾经的初中同学,和邻村一个人买树,在截锯树段时一不小心绊倒在锋利的油锯上,割裂,阵痛,以及无望的呼喊,终于还是失去了一条腿。那座旧年的学校还在,从平房改变为楼房,我每次回家时都会看上几眼——有些事物有些人,真的是看一眼少一眼。那些曾经的梦想呢,那些面对天空与大地喊出的豪言壮语呢,那些奔散的人呢,流落在天涯海角。我不是仇富——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情结,而是鄙视某些富人的形态(这里面绝对不掺杂任何葡萄酸的心理)。将相本无种,这句话让人质疑,在某个时段,某个地方,将与相绝对不是因为基因的存在而延续,而是继承了诸多因素:教育的,人际关系的,物质的,以及某些不能见光的蝇营狗苟。
和那位同学一个村庄的另外一个同学,几年前就已经心脑血管疾病偏瘫、离去。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他的场景和样子,谦卑的,弱小的,明显因为营养不良而显示出来的生命的枯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还是同学,小学时的同学,一个村,但不是一个生产队,我上学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村庄,后来遇见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所谓的情谊渐渐薄凉,我不信某些信誓旦旦的东西会一直存在,就像再美好的画面也会一闪而过,你留不住的,那么只剩下祝福,祝福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一路小心,一路照顾好自己。他也是一个买树卖树的人,本乡大力发展木业,曾经有一段黄金时间几乎每个做生意的人都富得流油,由此而去不远的县城桑拿洗脚抹牌豪赌,也有人金屋藏娇。这是资本的滥觞,也是金钱所带来的迷茫。树放倒了,砸在一家人的屋顶上,当时没塌下去,后来房主让给修缮,在爬上屋顶修缮时房梁垮塌下来,人坠落在地,登时没有了生命体征。富达平台
还有,运输木材的机动车由于司机喝酒发生车祸,人被压在下面;还有,吊车在协助锯树时树倒错了方位,迎面砸向驾驶楼;还有,拖拉机粉碎玉米秸秆时绊上了电杆拉线,司机被电线杆直接砸死,家里人清晨发现时早没了气息;还有,姜庄的一对老人有空调没开在密封的房间煤气中毒;还有,在木材加工时木头滚落下来砸在脑袋上,进了ICU病房现在还没出来;还有,更多的癌症患者在省城、北京、上海和家乡的医院里来回奔波……
金庸走了,著名主持人走了,奥兹走了——一年之间微信里充斥着各种死亡的气息,时间变得快了,好像死亡也离得近了。一些铺天盖地的信息,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贸易战还是某个大亨出柜都会引起潮水般的狂欢,仍然逃不过鱼的记忆只有七秒的循环,之后是短暂的沉默,之后是看起来的风平浪静,之后是某些巨婴式的岁月静好——
很让人尴尬,在这样的包围中书写变成了一个夹缝中自我寻欢式的短暂快感式表达——你要写下什么?你要留下什么?你要企图通过文字表达什么?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属于手艺人的作者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活着——一个词语中包含着太多的无奈和命运的驱使,以笔为刀么,还是从大先生手中战兢兢接过那把匕首?都会让人心生惶惑。
仍然是无奈的驱使,非关名利或其他,只是在命运的程式中我还有想要表达的欲望,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更为高尚的理由。集团式的狂欢在继续,树木变成纸浆又变成洁白的纸张又被印上油墨的文字。爱与黑暗之间,到底还有什么在过渡?看完电影也算是对亡者的纪念,我只记下这样一句话:“失望是梦想的本质。”《乡村生活图景》也早已读完,早已忘记,无非是时代的烙印之下,每个人在怎样生存——该怎样生存有时是无法选择的,就如一条河的流向,过去许多年,也还在原来的航道日夜流淌。
我是不是有些太过宿命,或者说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无非是一个几可被忽略的人或者浩渺宇宙中的某粒尘埃?富达平台
世界由无数个点构成,AI在以自己的方式诞生,奔跑、跳跃,在商场或银行大厅面无表情但声音魅惑地引领你进入下一个程序。会不会某天从梦中醒来,你也会发现自己已经机械成AI的模样,庄周与蝶,AI和你,已经很难分清。
我也在继续机械的生活,春种秋收,玉米收下来甚至没进院子就被连带玉米轴卖到粮食点,换来几张毫无表情的纸币。该打药打药,该浇水浇水,偶尔会去田野里看看它们是不是还是记忆中的样子。理发这个事儿,脑回沟里好像被忽略在一边,也是机械地拿起刀剪,该剪剪,该剃剃,该做成如何才能适配顾客的样子就做成怎样。
知交在天涯,活成你自己的样子,或者所谓的知交就是一个人内心与灵魂的镜子,彼此相对,无言而相知。有些话不说也罢,既然活成了最大公约数的存在,那么有些事情也毋需再来解释。刚才放朴树的《送别》,这首能让一个男人把自己唱哭的歌来自于更远更远的时空。“碧云天,黄花地。”先是范仲淹的吟哦,接着是王实甫《西厢》里的“【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后来才是李叔同的长亭短亭,接下来才是现代人模仿般的回声。我倒没说这样不好,就是在梳理某些东西的同时,发现流行之于传统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汪惠仁大人在给我的某个评奖词中说:作者选择了难度。我也会觉得是难度,但是兴趣使然也就管不了许多。越来越讨厌太多的注水文字(好像自己就不是了:存疑),越来越反感虚与委蛇,越来越感受到时间流逝之快,越来越明白所谓生命有时更接近一场假装正经的游戏……
你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念。想与念,两个朴素的字眼只能用灵魂的波动来给予注释,其他都是多余。想,可以穿越时间、地理与时空,如同梦境足以让人怀疑是不是另外一生;念,可以让人安宁也可以让人疯癫,在面对自己时也会心生悲悯——我要替你保管好自己,以便相见时,你能从我的眼中还能看见你的样子。
每个人都是一件易碎的物品。
还是不能免俗,在送别的同时我会想起那些被发表转载的文字,粗略统计,差一点点20万字;两本书已经出版:《慢时光,牵牛而过》《一群羊走在村庄的上空》;接下来是正在制作或者准备出版的炊事和节气,还在写什么——也就算了吧,反正我现在在每天看戏、读戏,装作学究般研究那些原本生疏的人间大戏,有团圆和离别,也有悲哀与欢喜(略有显摆的嫌疑)。
逝者已去,生者或在狂欢或在挣扎,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仍愿人间平安。富达平台
富达平台注册:www.sm2346.com